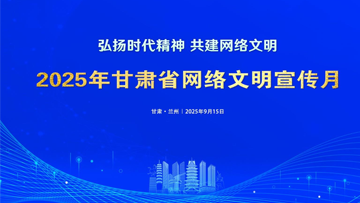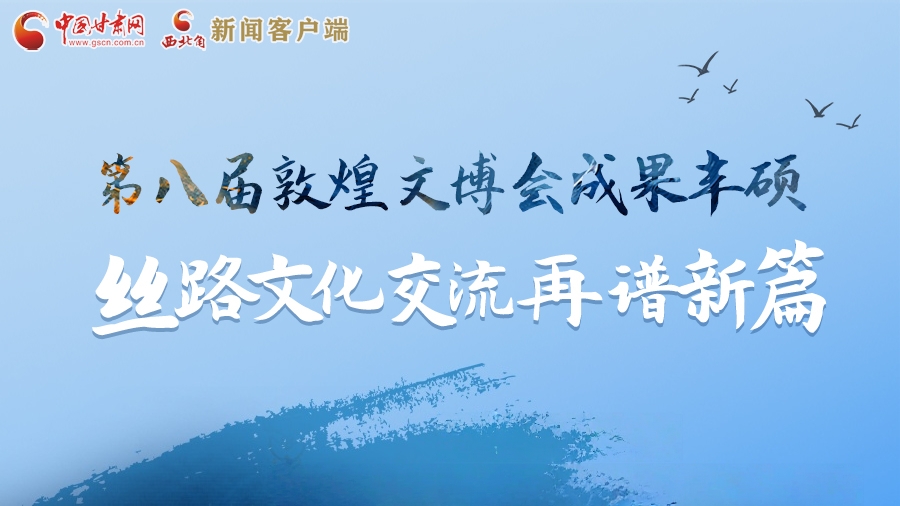今年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70周年。文化潤疆,是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截至2024年,新疆有登記備案博物館150家。游覽博物館與古遺址,是領略新疆人文之美的重要途徑。由北京援建的和田地區博物館,文物豐富、展陳創新,在中國歷史的大框架中全方位講述和田歷史,通過文物證明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歷代中央政權對其進行了有效管轄治理。
神秘的精絕古城出土了國寶級文物
走進和田地區博物館大廳,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幅巨大的畫,在雪山與沙漠的映襯下,位于畫面中心位置的“五星出東方利中國”錦護膊熠熠生輝。這件國寶級文物原件收藏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,出土于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。這件東漢文物以錦為面,白絹包緣,色彩鮮艷,錦面上用藍、紅、綠、黃、白五種顏色,織出云氣紋、瑞獸紋等紋飾,紋飾之間織有“五星出東方利中國”八個漢字。這件織物的經緯線密度遠大于普通漢魏織物,代表了當時織錦技藝的最高水平,有學者認為這件織物應為蜀錦,蜀地工匠應漢朝宮廷之命制造,最終它出現在尼雅遺址一座墓葬的墓主身上。
尼雅遺址,即是漢代西域三十六國中的精絕。公元前60年,漢朝設置西域都護府,開創中央政權有效管轄治理新疆地區先河。正史《漢書》與《后漢書》中都有《西域傳》,《漢書•西域傳》如此介紹精絕:“精絕國,王治精絕城,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。戶四百八十,口三千三百六十,勝兵五百人”;“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,南至戎盧國四日行,地厄狹,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”。《漢書•西域傳》中對西域各國的記載,都會標出從長安到此地的距離和從西域都護府到此地的距離,這是漢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治理的鮮明體現。
和田地區博物館基本陳列之一“漢晉子民——精絕人的繽紛世界”,向觀眾呈現了尼雅遺址的考古成果。尼雅遺址深居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,發源于昆侖山北麓的尼雅河為精絕人的生活提供了水源,有此水源精絕人得以發展農業。考古學者在尼雅遺址中發現了一枚東漢的煤精印章,印面刻有“司禾府印”,這是東漢在精絕設立屯田機構的證據。歷代中央政權都十分重視在西域發展屯田,漢代始創西域屯田,此后不斷擴大。中原人將先進的農業技術帶到西域,屯田不僅提高了西域農業生產水平,也使得漢族與西域各民族相互了解、共同發展、民心相通。
尼雅遺址中有馕坑和冰窖,得益于極度干燥的氣候,觀眾甚至能看到盛羊頭的木盆、盛羊腿的木盆、盛梨的單耳木杯。小麥制成的馕、牛羊肉、梨、葡萄等是精絕人的日常食物。以食物放于食器中隨葬,不僅是精絕人的葬俗,也可見于新疆許多重要遺址。
精絕人是技藝精湛的木匠,他們在綠洲中打造木屋,制作木家具和生活中會用到的木碗、木盆、木杯、木器座等,在木門和木家具上,精絕人會雕飾華麗的花紋,盡展對生活的熱愛。和田地區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雕花木柜門便是精絕人的杰作,木柜門淺浮雕有精美的圖案,居上的圖案刻畫一個人牽著大象,象鼻卷起,象背上還放置墊子可供人坐,居下的圖案刻畫一只有翅膀的怪獸,它頭上有角,從頭部到翅膀處刻畫出鱗片,尾巴上翹,似龍又非龍,圍繞這兩個圖案的是麻花紋、菱格紋、草葉紋等紋飾。這件不大的木柜門,卻透露出深居沙漠的精絕人,與南亞、西亞存在著文化交流,或許正是絲綢之路將其聯系了起來,遠方的器物與文化不再遙遠,而是成了日常起居之物的裝飾。
于闐與中原通過玉石與絲綢緊密聯系
公元4世紀后期,精絕神秘消失了,精絕人去向不明,時至今日,學者們對于精絕消失的原因莫衷一是。而漢代西域三十六國中的于闐,則一直持續到11世紀初。和田地區博物館基本陳列之一“五星出東方利中國——和田歷史文化陳列”以恢宏的篇幅、多元的視角、豐富的文物介紹了和田歷史變遷、這片土地上生活的各民族及其創造的文化、歷代中央政權對和田的有效管轄治理。
和田,古稱于闐。于闐是絲綢之路南道上的重要樞紐。其實,早在張騫鑿通絲綢之路前,于闐已經與中原有了緊密的聯系,聯系的紐帶是和田玉。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中出土的許多精美的玉器,就是以和田玉為原料的。和田玉,被譽為“昆侖山的心”,當它通過“玉石之路”源源不斷輸入到中原時,也贏得了中原人的心,對和田玉的喜愛,從古延續至今。
故宮寧壽宮樂壽堂中安放著一座清朝乾隆時期的玉山,雕刻《大禹治水圖》,大禹治水改堵為疏、與民同勞、為國忘家,這一題材具有深厚的政治內涵,而這座玉山的制作歷程,也表現了團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調度能力。玉料來自和田密勒塔山,清宮造辦處據宋人的《大禹治水圖》進行設計,揚州的工匠耗費六年時間將其雕刻完成,最終將它安置在紫禁城中,迄今已有兩百多年。
和田地區博物館中陳列了大量古代文書,一件唐代于闐文“思略租賃桑樹契約”文書值得特別注意。這是一件寫在紙上的契約,使用的是于闐文。大約在公元4世紀,于闐人借用婆羅謎字母創造了于闐文來書寫于闐語,它廣泛運用于契約、賬目等民間文書中。這件契約說的是一個叫思略的人向一個叫漢卡的人租賃桑樹,租期一年,租金是三匹于闐本地特有的絲織品。思略租賃桑樹是為了養蠶制絲,而絲織品可以作為貨幣來使用不僅是于闐的習慣,也是絲綢之路沿線許多地方的習慣。
約在公元3世紀,中原的養蠶繅絲技術就傳播到了于闐。關于這項技術如何傳入于闐,曾到訪于闐的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記》中記錄了一個迷人的傳說,玄奘稱于闐為瞿薩旦那,“昔者此國(指于闐)未知桑蠶,聞東國有也,命使以求”,初求不成,“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,求婚東國,國君有懷遠之志,遂允其請”。于闐王派使者到中原迎親,希望公主能將蠶種帶回于闐,造福于闐百姓。公主將蠶種放在帽子中帶回了于闐,并將養蠶繅絲的技術教給于闐人,還立下“不令殺傷,蠶蛾飛盡,乃得治繭”的規矩,自此之后,于闐桑樹成蔭,絲織業蓬勃發展。在和田地區策勒縣丹丹烏里克遺址中,曾發現一幅《東國公主傳絲圖》木板畫,原件已被英人斯坦因盜去,在和田地區博物館中可以看到復制件。畫面中東國公主典雅端莊,旁邊一位侍女手指她的帽子,暗示其中藏著蠶種。
“開于闐,綿綾家家總滿。”這是敦煌民謠中的一句歌詞。在于闐等地,絲綢經過扎染后,形成了至今仍深受維吾爾族同胞喜歡的艾德萊斯綢,那明麗的顏色,仿佛跳動的音符,且歌且舞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。
于闐的繪畫與音樂深受唐人的喜愛
唐代,中央政權對西域的有效管轄治理進入一個新階段。唐代先后設置安西大都護府和北庭大都護府,統轄天山南北。安西大都護府下設龜茲、于闐、焉耆、疏勒四鎮,在于闐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軍事鎮防體系。唐朝的典章制度、文化藝術對于闐產生了深刻影響。
與此同時,于闐的繪畫樂舞也深受中原人的喜愛。唐朝宮廷中有兩位來自于闐的畫家,一位叫尉遲跋質那,另一位是其子尉遲乙僧,時人稱活躍于隋代的尉遲跋質那為“大尉遲”,稱活躍于唐初的尉遲乙僧為“小尉遲”。兩位畫家皆以繪制寺廟壁畫為能事,他們帶來了西域的繪畫技法,為兼收并蓄的唐代畫壇所注目,唐代張彥遠的《歷代名畫記》記載他們擅長畫西域人的形象及菩薩的形象,“小則用筆緊勁,如屈鐵盤絲,大則灑落有氣概”。可惜的是,兩位畫家的傳世作品少之又少。和田地區博物館展出的大量本地古代佛教遺址壁畫,或許能彌補我們的遺憾,使我們得以一窺古代于闐繪畫藝術取得的成就。
于闐是絲綢之路南道上重要的佛教中心,玄奘對于闐印象深刻,對這里的民俗很有興趣,《大唐西域記》稱于闐“國尚樂音,人好歌舞”,音樂與舞蹈是于闐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唐代詩人李賀有一首《李憑箜篌引》,寫的是他聆聽李憑彈奏箜篌的感受,到底是詩壇的鬼才,李賀下筆即不同凡響,他寫箜篌的聲音是“昆山玉碎鳳凰叫,芙蓉泣露香蘭笑”,這箜篌聲如仙樂一般,不僅令在場的聽眾神往不已,傳入天界更令女媧、吳剛忘記了自己的職守,“女媧煉石補天處,石破天驚逗秋雨”,女媧忘記了補天,使一場秋雨從天而降,“吳質不眠倚桂樹,露腳斜飛濕寒兔”,吳剛忘記了伐樹,在桂樹下聆聽箜篌聲,玉兔也入迷地聽著,寒露打濕身體也未注意到。
箜篌中的豎箜篌非中原本土所有的樂器,和田地區洛浦縣山普拉墓地曾出土一件漢晉時代的木質豎箜篌,而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縣的扎滾魯克墓地出土過兩件距今約2700年的木箜篌。豎箜篌從西亞傳入西域,隨著西域歌舞再傳入到中原。
絲綢之路上文化交流的頻密,經常超過我們的想象。在和田歷史文化陳列的最后,觀眾可以看到一件出自洛浦縣比孜力佛寺遺址的人物紋栽絨毯,它上面繪制的是什么人物,講述的是什么故事,已故北京大學教授段晴經過仔細研究后,認為講述的是兩河流域流傳的史詩《吉爾伽美什》。
“一唱雄雞天下白,萬方樂奏有于闐”,這是毛澤東同志1950年10月創作的《浣溪沙•和柳亞子先生》中的兩句。而今,進入新時代的新疆,各項事業在黨的領導下取得歷史性成就、發生歷史性變革。2022年正式對外開放的約特干故城景區,是近年來和田地區最受歡迎的文旅項目,距景區幾公里處的約特干遺址,很有可能是古于闐的都城。當夜幕降臨,在復原的約特干故城中,行進式的歌舞表演歡迎四方來客,于闐歌舞魅力不減、更加動人。(陳彧之)
- 2025-09-23強化政治監督,推動高質量完成“十四五”答卷 一體化 一條心 一起干 同譜區域發展“協奏曲”
- 2025-09-23銘記歷史 開創未來
- 2025-09-23廣安觀潮 | 黨政機關帶頭過緊日子是為了老百姓過好日子
- 2025-09-23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加速融合 新質生產力蓬勃發展 科技強國根基不斷夯實

 西北角
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
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
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
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
今日頭條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