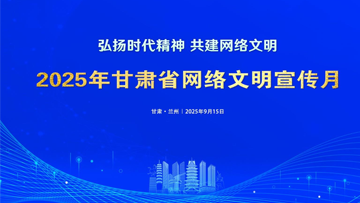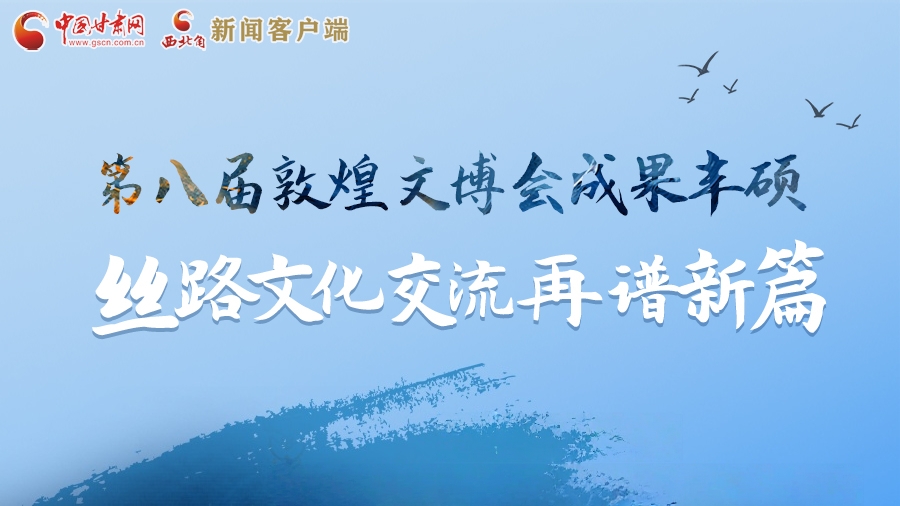原標題:擺脫“學歷焦慮” 重新定義成功
編者按
當前,一些年輕人受困于“學歷出身”問題,面對部分用人單位對名校和高學歷的明顯偏好,他們不時陷入自我懷疑與焦慮之中。高學歷的人更容易成功嗎?青年如何建立與時代發展相契合的成功觀?
主持人:
許子威 中青報·中青網見習記者
嘉賓:
杜玉華 教育部“長江學者”特聘教授、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
李乾坤 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
耿品 中國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
主持人:沒有名校高學歷,就是失敗嗎?思政課如何引導“學歷焦慮”的年輕人在國家發展格局中,認識到自身的潛力和優勢?
杜玉華:人們往往把“貢獻”局限于高精尖行業,而忽視了社會結構多元、分工各異的復雜性。國家的發展離不開億萬普通勞動者的堅守與創造——每一個崗位都具有其獨特且不可替代的價值。無論是基層治理、鄉村振興,還是制造與服務一線,每一位勞動者的付出都是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的支撐。
在思政課教學中,我注重引導學生從宏大敘事回歸微觀實踐。一是解構“貢獻”的多元形態,結合學生所學專業,闡明其行業在國家發展中的實際作用,將抽象使命轉化為可感知、可踐行的職業目標;二是幫助學生識別并發揮自身優勢,許多學生在實踐能力、溝通協作與社會適應力等方面具備特長,這些恰恰是社會轉型與產業升級所需要的重要素養,應有意識地加以發掘和強化,從而提升就業信心與競爭力;三是強化責任感與使命感,引導學生深入理解個人發展與國家命運之間的內在關聯,激發內生動力,走出“學歷焦慮”,走向積極有為的人生。
耿品:在思想道德與法治課上,我會告訴學生,評價人生價值應全面考量——既要看貢獻大小,也看努力程度;既尊重物質貢獻,也尊重精神貢獻;既注重對社會的奉獻,也注重對自我的完善。對人生價值的評判,絕不是僅憑學歷高低或某一單項指標簡單斷定。
當前部分年輕人出現的焦慮心態,既源于外界以院校、成績、獎項等作為單一評價標準,也來自主體意識尚未完全建立的大學生,將這些外部標準內化為自我認知,導致其在角色認同過程中感到困惑與迷茫。
因此,思政課教師可以從兩方面著力:一方面,幫助學生全面客觀地認識自己,增強自我認同。教師應引導他們認清自身在不同場域中的角色定位,理性看待自身能力、特質與關系網絡,鼓勵學生以持續發展的心態踐行每一種角色;另一方面,引導學生理性看待“鏡像反饋”,正確處理外界評價。教師應及時引導學生主動調適心態,在積極回應社會期待的同時,成長為更好的自己。
主持人:思政課如何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擇業觀,特別是將個人理想與國家需要和社會發展相結合?
李乾坤:馬克思在《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》中寫道,在選擇職業時,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。
如果用高學歷、高薪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成功與否的話,馬克思看起來并不算“成功”。他畢業于柏林大學,擁有博士學位,但并沒有“高薪”的工作,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過著貧困的生活。但馬克思一生踐行為人類幸福而工作的理想信念,將有限的生命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無產階級及全人類的解放事業。因此,馬克思主義價值觀與追求“名校”“高薪”有著本質區別。
耿品:在大一上學期的思想道德與法治課程中,“如何把握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關系”“為什么要堅持‘為人民服務’的人生追求”等內容,既是教師教學的重點,也是學生學習的難點。剛進入大學的學生理論知識儲備不足,實踐經驗較為缺乏,對馬克思主義人生觀的科學性和正確性難以形成深入理解。針對這一情況,在教學中我會采用“小切口”進入的方式,通過身邊人、身邊事闡釋“大道理”。例如,講述中國農業大學青年學子扎根科技小院、“自找苦吃”的實踐案例,幫助學生感悟理論力量與實踐價值。
主持人:有人崇拜高學歷,但也有部分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以“985廢物”自嘲,反映出他們怎樣的心態?
杜玉華:這兩種心態看似矛盾,折射出社會轉型期價值評價體系的單一化,以及青年群體身份認同的焦慮。一直以來,名校被視為一種稀缺資源,與個人成功緊密綁定,因此很多家長、學生出現了“第一學歷”的擔憂。而部分名校學生自嘲為“985廢物”,反映出了他們面對現實落差時的無力感——即便擁有光環,仍可能無法實現預期成就。這些年輕人并非失敗者,只是害怕辜負社會、家庭的期待。因此,教育的導向不能僅聚焦于“考高分”“上好學校”,更應重視“如何成為更優秀的人”。
李乾坤:這源于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不同人生路徑的誤區。社會常以量化標準預判個人發展,如分數、學校、排名等,卻忽視了高校和專業類型、定位和培養目標的多樣性。如果一所高校和相關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并非今天的“風口”行業,學生和家長若無法調整預期,就會出現心理落差,也就產生了“985廢物”自嘲。
耿品:“985廢物”這類自嘲其實是部分青年用一種戲謔的方式來“反諷”自己,由此來釋放壓力、尋求認同。他們背負著家庭、社會的高期待,當實際成就與之不符,便通過自嘲緩解焦慮,并希望在群體共鳴中獲取理解與包容。
主持人:大學生應如何定義“成功”?
杜玉華:名校學歷與職業成就、人生發展存在一定關聯,但并非決定性因素。真正影響職業高度的,往往是個人的學習與實踐能力、對行業機遇的敏銳把握,以及整合社會資源的能力。而人生幸福感的獲得,更依賴于個體的價值取向、人際關系的質量以及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。現實中,許多普通高校畢業生正是通過持續努力,不斷實現職業上的突破。
因此,引導青年重新定義成功,需要家庭、學校、社會協同努力,共同構建更加包容、多元的成長環境,支持年輕人在探索中找準人生坐標。這意味著要從追求“外在指標”轉向注重“內在體驗”——成功不應僅以收入或職位衡量,更應看內心是否充實、自我是否認同、生活是否自主、工作是否有價值,以及人生能否在多重維度中保持平衡。同時,成功也應從注重“占有”轉向強調“創造”,其核心不在于獲取多少資源,而在于為世界貢獻了什么價值。無論是攻克關鍵技術難題,還是在平凡崗位上盡職盡責,這種由創造所帶來的意義感和滿足感,遠非物質所能替代。
耿品:成功并沒有統一的標準。在與青年學生的交流中,我發現他們往往容易受到外界標簽的影響,從而形成對“成功”多元而流動的理解。因此,年輕人與其糾結于是否達到外界定義的“成功”,不如更多地思考如何在實現人生價值的過程中獲得成功。在這個過程中,思政課教師應當引導學生認識到服務人民、奉獻社會的重要價值,幫助他們理解積極進取、務實樂觀的人生態度對成功的重要意義。
主持人:不少非名校大學生靠努力實現了突破,這些年輕人的故事有哪些普遍性和可復制性?
杜玉華:現實中,不少非名校畢業生成功實現了“逆襲”——有的投身新興行業,有的憑借精湛技藝在制造、服務等領域脫穎而出。雖無名校光環加持,但他們往往更善于把握機會、作風踏實、適應力強,不斷拓展出自己的職業發展路徑。這些故事之所以引發廣泛共鳴,正是在于它們打破了“名校即成功”的單一敘事,展現出普通青年同樣可以通過努力與創新,贏得社會的認可與尊重。
盡管具體個案難以簡單復制,但其成功邏輯具有普遍參考意義。我認為以下幾個要素尤為關鍵:一是實踐導向。他們更貼近現實,更愿意從基層做起,注重將知識轉化為實用技能,并在真實環境中積累經驗;二是韌性心態。面對社會偏見與壓力,他們通常更能放下身份包袱,較早學會承受挫折,并主動尋求差異化成長路徑;三是社會感知力。他們大多善于觀察社會、深入基層,深刻理解社會運行機制與大眾需求,從而更敏銳地捕捉轉型中出現的新機遇。
主持人:越來越多的青年學子自覺選擇到基層受鍛煉、長才干、作貢獻。思政課如何幫助學生正確理解“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”的意義,并堅守這類選擇?
李乾坤:“扎根基層”“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”體現的是一種超越個人功利層面的價值追求。它意味著青年主動將個人成長與國家戰略、人民需要緊密結合,真正把青春奮斗融入家鄉改造、鄉村振興和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中。這不僅是對人生意義的深層理解,更是對“成功”定義的重新校準。事實上,基層一線是國情社情最真實的地圖,也是青年成長最肥沃的土壤。在那里,年輕人能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獲得真正的能力提升與價值實現,進而獲得持久、堅實的成就感和幸福感。
認識到這一點,學歷焦慮自然得以緩解。名校背景或高薪職位只是人生一個階段的標簽,并不能定義人的全部價值,真正重要的是能否找準自己的坐標,在現實土壤中生長出不可替代的能力。因此,年輕人選擇基層不是放棄追求,而是換一種方式更好地成就自我、服務社會。它代表了一種清醒的人生規劃,一種將“小我”融入“大我”的成長智慧。
耿品: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的沖鋒陷陣,還是和平建設時期的默默奉獻,到基層去、到一線去、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,始終是青年成長成才的重要途徑,也是推動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源泉。
在思政課堂上,我常常通過歷史與現實的對話,展現這種選擇的時代意義。如在新中國成立初期,青年響應號召奔赴北大荒,使昔日的“北大荒”變成了“北大倉”。如今,青年學子選擇成為一名西部計劃志愿者,將個人理想與國家需要同頻共振。
不同時代的青年都作出了同樣的青春選擇。當前,鄉村振興戰略、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等政策的實施,為青年深入基層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。在這個過程中,青年既能錘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,又能培養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,從而更好地認識自身在國家發展中的定位和價值。
(中青報·中青網見習記者 許子威 記者 王聰聰整理)
- 2025-09-282025年福州文旅嘉年華啟幕 “情緒+文旅”催生新賽道
- 2025-09-28黃梅戲“骨子戲”銀幕新生 數字電影《羅帕記》在京首映
- 2025-09-28(文化中國行)第十九屆中國戲劇節的經典煥新與時代回響
- 2025-09-28“林芝文旅號”首航落地 助力西藏打造世界級旅游目的地

 西北角
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
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
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
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
今日頭條號